内容提要:随着西方国家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者社会的转型,旅游消费已发展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种基本需要。社会学家关于旅游消费现象的研究提出了旅游消费的本真论、享乐论、日常实践论、文化宰制论和制度激励论等代表性解释。其中,“本真论”和“享乐论”从微观视角解释了旅游者个体的不同体验,“日常实践论”从中观视角解释了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之间动态的互动过程,以及对旅游者的日常生活世界产生的影响;“文化宰制论”与“制度激励论”则从宏观视角解释了旅游消费的社会分层机制和外部激励因素。这些观点对分析转型中国的旅游消费现象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
关 键 词:旅游消费/本真论/享乐论/日常实践论/文化宰制论/制度激励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国家从生产型社会(以生产为核心)向消费者社会(以消费为核心的大众消费时代)的转型,旅游消费不仅发展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种基本需要,也逐渐成为很多国家的支柱产业之一。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旅游消费现象进入社会学研究的视野则是晚近的事。
大多数专业社会学家曾认为,社会学应关注“严肃的”、“有用的”和“重大的”社会问题,而旅游现象被视为琐碎的、肤浅的社会现象,没有太多的研究价值。更有甚者,一些社会学家认为旅游消费是一种经济行为,因而也只是经济学研究的课题。后来,伴随着大众旅游的兴起,社会学家发现,并非只是经济因素影响了旅游消费行为的发生,很多如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等非经济因素也是影响旅游消费的重要方面,故此,旅游消费才作为一个重要问题逐渐进入社会学的研究视野。
英国社会学家洱瑞指出,旅游决不是在社会学意义上“无意义”的、“琐碎”的现象,而是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1]。社会学家围绕人们为什么去旅游这一基本问题,主要提出了旅游消费的本真论、旅游消费的享乐论、旅游消费的日常实践论、旅游消费的文化宰制论和旅游消费的制度激励论等几种重要观点。本文试就以上观点进行梳理,并分析转型中国的旅游消费存在的不足。
一、旅游消费的社会学解释
(一)本真论
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麦坎内尔首次提出用“本真性”概念来解释人们的旅游消费现象。他指出,旅游是一种与宗教朝圣对等的神圣活动,更确切地说,是人们远离现代社会而去追求“真实”的世俗的朝圣,这种真实是与原始社会的神圣性相对而言的。在麦坎内尔看来,由于现代社会生活的肤浅性和体验的非真实性,使得旅游者离开自己生活的世界,前往“异地”或“他时”找寻一种现实生活难觅的“本真性”体验[2]。
后来,受社会学家戈夫曼“戏剧”理论的启发,麦坎内尔又进一步用“舞台化的本真性”来发展他的“本真性”概念,他认为旅游者追求的“本真性”即是戈夫曼提出的“后台”,“后台”是与神秘感紧密相连的,神秘感可以促使旅游者得到一种真实性的体验。然而,“现在所展示给游客的已不是那些如戈夫曼所定义的一般‘后台’,而变成了‘舞台化了的’(展示的)后台”[2]。这样的“后台”是专门为旅游者的需要而炮制出的“本真性”。这也正如布尔斯丁提出的“虚假事件”[3]一样,认为人们很难通过旅游过程获得“本真性”体验,因为旅游场景本身往往会是一种虚假的设计产品,导致旅游者首先获得了一种虚假的人工设计的经历或体验,让旅游者追求真实体验的初衷动机被预先布置好的、非真实性的产品所替代了。科恩也对麦坎内尔的“本真性”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真实性”被赋予了给定的或者“客观的”性生质,被现代人用来形容“远方的”世界。亦即,“本真性”是一个在社会中建构起来的概念。如此,这样的“本真性”不是既定的,而是“可商议的”[4]126。
尽管如此,麦坎内尔的“本真性”还是成为被广泛用来解释旅游消费现象的一个重要概念,国际学术界关于旅游中的“本真性”研究也因此而成为旅游社会学研究文献增长最快的领域之一。为了深入讨论对“本真性”概念的理解,许多社会学家试图重新建构“本真性”的内涵。科恩根据个体在旅游中寻求到的体验深度的不同,将旅游者的体验分为五种模式:即娱乐模式、转移模式、体验模式、实验模式和存在模式。娱乐模式下的旅游者依附于他的社会或文化中心;转移模式下的旅游者周游在没有中心的天地里;体验模式下的旅游者失去了他们自己的中心,无法在自己家里找到一种真正的生活,力图通过与他人共鸣的、本质上是审美的方式,去体验他人生活的真实;实验模式下的旅游者是那些不再愿意依附他们自身社会的精神中心,转而向四面八方去找寻替代中心的人;存在模式下的旅游者则是依附于“选择的”中心(与日常生活世界相对而言,定期出发去朝圣并获取精神支持的地方)的人[4]79-106。不难看出,科恩的“五种体验模式”扩展和丰富了麦坎内尔关于旅游体验的“本真性”内涵,即从“肤浅的”、被单纯寻求“乐趣”的愿望推动的旅游,走向“深刻”的、被寻求意义推动的旅游。
著名消费社会学家王宁教授认为,从旅游目的地来看,可以将旅游体验的“本真性”划分为:客观主义的本真性、建构主义的本真性和存在主义的本真性三种类型。客观主义的本真性是指对原作品的真实性体验。相应的,旅游体验中的“本真性”相当于对原作品真实性的认识论体验。建构主义的本真性是指为旅游者设计的、或是旅游开发商根据游客的意象、期望、偏好、信仰、权力等建构出来的旅游客体。存在主义的本真性是指旅游者在某些旅游活动的激发下,处于一种潜在的“成为”的存在状态。相应的,旅游体验的本真性是为了在有限的旅游过程中获得这种潜在的“成为”的存在状态。存在主义的本真性与旅游客体的真实性毫不相关[5]。此后,王宁按照游客的体验又将“本真性”分为“单向本真性”和“互动(双向)本真性”两个方面[6]。在他看来,以往研究多把“本真性”当作一种“单向本真性”来对待,“即一种存在于旅游对象中的、有待游客去观察和发现的本真性。与此同时,游客被假定为只是被动的观众,不是参与建构旅游本真性,并围绕本真性与旅游对象进行互动的主体。”与之相对应,“互动本真性”则是一种源于旅游客人和本地东道主的接触、互动和交流的本真性。此时游客是主动的、积极参与的,并卷入了自己的感情[6]。即游客参与当地人的合作是“互动本真性”得以产生的条件。
(二)享乐论
在传统社会,人们的消费欲望是被一种特定的消费观念所抑制。韦伯笔下的新教教义说道:按照上帝的意志:“只有行动,而不是消闲和享乐,才能够增加上帝的荣耀”,如果“把时间损失在社交、闲聊、奢侈生活方面,甚至睡觉超过保证健康所需的时间(六小时,最多八小时),是一定要受道德谴责的”[7]148。换言之,人们对非必需品的消费被视为是一种浪费行为,甚至是一种可耻的行为。享乐伦理在这种时期是被污名化的,禁欲不仅被赋予了强烈的道德色彩,还被赋予了浓厚的宗教色彩。也就是说,只有“劳动是一种公认的禁欲手段”[7]146-147。相应的,一切与劳动无关的享受性生活方式都被视为不合理的。作为一种“非必需品”消费——旅游消费,在这种消费观念下自然不会被提倡,甚至可能是禁止的。
随着西方发达国家从工业社会进入消费社会,享乐伦理逐渐兴起,并成为消费社会的典型特征被广为接受。“享乐伦理兴起的一个标志是享乐不再具有道德的贬义,而是获得了文化合法性。”[8]346享乐伦理的“合法化”催生了“后现代旅游”(大众旅游)的出现[9]。如此,麦坎内尔关于旅游消费的“本真性”解释也受到了挑战,寻求享受和快乐才是现代社会旅游消费兴起的主要成因。换言之,如果说早期的旅游是为了“寻真”甚或“逃避”现实生活方式的话,那么现代旅游(大众旅游)则更多为了去享乐,享乐的“正当性”是大众旅游消费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前提。享乐的“正当性”主要包括:享乐是人生的目的;享乐是减轻工作压力的手段;追求享乐是奋斗的动力;享乐是付出努力的回报;享乐是国家所允许和鼓励的事情[8]347。
如此这般,在消费社会,作为非必需品的旅游消费被合法化了,旅游消费的合法化是建立在享乐伦理(或浪漫伦理)合法化的基础之上的。导致享乐伦理滥觞的主要原因是经济的繁荣、收入的增长和中产阶级的兴起。正如波德里亚所言,“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风盛现象。”[10]1物质的极大丰富诱导着人们从一个物品走向另一个物品,或从一套消费体系进入另一套消费体系。在这种情形下,只有消费、享受才能体现物质丰富的价值[10]24-30。同时,随着中产阶级的兴起,在中产阶级或更多的富人那里,旅游消费成为“值得的”、“可接受的”、“不可替代的”、“最舍得花钱的”一种消费方式,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大众化的生活方式[8]367-369。另外,现代社会信贷制度的推广,还出现了一种新的消费趋势:超前消费,甚或是透支性消费。这种以提倡及时享乐为主的“观念性高消费”[8]313方式的逐渐盛行,使得享乐主义也得到了大众消费的认同并成为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
(三)日常实践论
特纳指出,旅游消费并非一定为了去“寻真”或享乐,旅游消费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类似于日常生活的实践,这一实践过程几乎涉及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全部方面,从吃、住、行到游、购、娱,旅游者体会了不同的消费感知。旅游者离开日常生活的“价值中心”,到“远处的中心”可以无拘无束地体验生活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11]。科恩更是具体地把现代旅游的通感认识细化为“视、听、嗅、味、声、触”等多个方面[12]。质言之,旅游消费并不是有“规定”的具体目标,旅游消费的实践过程本身就是旅游者的意义所在。
旅游者通过旅游消费的实践过程,让旅游主体的生活空间被扩展成了两个空间:“日常生活”空间和“选择的”空间(旅游目的地)[4]95。这样,旅游实践不仅扩展了旅游主体的生活空间,也改变了旅游主体的生活世界。但是,“出游是为了返回,每一次出游都给‘家’赋予了一次新的意义。”[13]也就是说,每一次旅游归来,“家”就会被重构一次。即通过对“选择的”空间的体验,旅游者获取了充分的精神过滤,再重返至“日常生活”空间时,更觉得“日常生活”空间才是真正的家园。
如此看来,旅游消费不仅是旅游者为了“寻真”或享乐,而是为了延伸自己的日常生活空间,让固有的日常生活焕发新的活力。旅游者“是出于自愿、暂时离家外出的旅行者,他们之所以从事路程相对较长的、非经常重复的往返旅程,是出于盼望旅行中能体验到的新奇和生活变化所带来的愉悦。”[4]29旅游者通过每一次出游,在短暂的过程中释放对现实的不满和怨恨、消除日常生活中的不适,从而在返回后更好地适应日常生活。
当然,旅游消费的日常实践也产生了一种“非预期后果”[14]。从旅游主体与旅游客体的互动关系来看,一方面,旅游主体为了拓展自己的日常生活世界前往旅游目的地参观某项“吸引物”,无论这“吸引物”是自然的还是人造的;另一方面,旅游客体(旅游服务者)也不断通过自己的工作来建构这个“吸引物”的“真实性”,使它们“适于”大众旅游消费实践过程的发生[4]51。这样,旅游消费在改变旅游主体的生活空间的同时,也改变着旅游客体的工作空间。例如旅游企业在提供旅游设施或旅游服务时,已经设定好了各种让旅游者们可接受的“吸引物”,众多被建构起来的旅游“吸引物”,就是为旅游消费者们的需求欲望量身定做的。如此这般,旅游消费在这里掩蔽了旅游“产品”的生产过程,旅游消费实践的过程使旅游“产品”的生产与消费同时完成。
(四)文化宰制论
著名社会学家里茨尔精辟地指出:在美国,旅游如同其他消费品一样,也被纳入了“麦当劳化”(即一种套餐式、注重效率、可计算性、可预测性、非人格化的“理性化”消费方式)消费特征的轨道。里茨尔批评这种消费特征存在着“理性中的不合理性”的悖论[15]58。“这方面最好的例子就是组团旅游。这儿可以举一个三十日游欧洲的例子,为提高效率,旅游者只访问欧洲主要的景点。游客匆匆地穿越一些城市,让游客在所允许的时间里尽可能多看一眼不同的景点……在那里,观光者可以匆匆地穿越景点,拍照、买纪念品,然后赶回旅游巴士再走向下面一站。团队旅游可以看作是一种得以高效地将人们从一个旅游点清运往另一个旅游点的机制。”[15]93质言之,在里茨尔看来,这种套餐式旅游往往只注重数量,注重游览了多少景点,而不是景点游览的质量如何。
这样,消费社会的旅游消费不仅是旅游者寻求“本真”或“享乐”的主动选择的实践过程,而且往往是被某种主观文化(消费文化)宰制的结果。让旅游者体验了一种社会学家齐美尔所言的“文化的灾难”,即: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正日益被自己创造的文化产品所压抑,具有文化意义的旅游消费原本是旅游者暂时逃离刻板化的日常生活的替代方式,但事实上,旅游者在旅游实践中却不得不遭遇了一种独特的消费文化的宰制[16]。
1.旅游消费受制于一种流行大众文化的操纵。“不论是穷人还是富人,不论是年轻人或是老年人,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所有社会成员都被身边的这种大众文化的变迁所触动。”[17]70-71例如,“组团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普遍的主流大众文化形式,组团旅游是人们后天创造的一种“主观文化”,其出发点是为人们的出游带来便捷和较为系统的服务,但事实上,组团旅游却偏离了初衷,非但让出游者没有享受到基本的精神愉悦,而且还被剥夺了更多的自由,让旅游过程变成了一种无意识的追寻“虚无之物”的消费活动。“虚无之物”即是指没有内涵,没有特色,没有个性,某个中心建构和控制、相比而言缺乏特定内容的社会形式,是与“实在之物”相对而言的。随着“虚无之物”扩张,“实在之物”被逼在角落和夹缝中生存,结果是空前的富裕到来后,曾经的有意义的重要世界消失了或被扭曲了[18]。例如,电子类导游这一方式被许多旅游景点(主要是博物馆、纪念馆等室内景点)所采纳,游客可以通过个人喜好及资费的高低来选择电子类导游或专业导游。一般来说,这种电子类导游价位低廉,介绍内容是事先程序化设定的,并无个性服务的特征。
2.旅游消费也受制于一种特定的符号文化的操纵。现代社会的旅游消费也是“一种符号的系统化操控活动”[19],这种“符号文化”也是另一种“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不但是改变消费者主观性的强有力工具,而且能够在各社会阶层中构建统一的消费愿望和消费品位。”[17]71换言之,人们消费的并不是对象本身,而是它所代表的符号。人们是否外出旅游,去哪里旅游,并非完全出于本能的需要,很有可能是受各种广告传媒的影响、亲朋好友的推荐、旅行社的促销手段等一系列符号文化的影响。
3.旅游消费同样受制于一种能够衡量社会身份认同或社会地位差异的标志性“产品”的操纵。“当主流社会都在使用某种产品或实践某种生活方式时,如果某人无力使用这种产品或实践这种生活方式,他必然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8]318也就是说,在大众旅游盛行的现代社会,如果一个个体无力去外出旅游,便会使其产生一种挫败感。于是,此时的旅游消费已不再只是一种实践体验,而变成了一种衡量个体社会身份或社会地位的“产品”。如此,人们通过旅游消费活动可以获得一种新的身份认同,或体验到一种“我们”与“他们”之间的身份差异。正如丹恩所发现:西方人,尤其是中下阶层,可借旅游体验第三世界目的地居民的伺候、羡慕和尊敬,来“提升”自己的地位[20]。换言之,在消费社会中,许多人去旅游消费不是出于人们生活的必须,也不是为了传统的展示需要,而是为了获取他们的某种身份认同[21]。
(五)制度激励论
如果说,旅游消费的“文化宰制论”反映的是,旅游者去旅游是因为受制于某种外部因素的被动约制,那么旅游消费的“制度激励论”则着重反映了某种外部因素对旅游消费的积极推动过程。具体而言,与西方国家的消费逻辑不同。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社会大规模的旅游消费的兴起,更多的是受一种外部宏观制度激励的结果。因此,“制度激励论”是关于转型中国社会大众旅游消费的重要解释。正如王宁指出的:“在一个全能主义国家,消费并不仅仅是个人层面的事性,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政策和制度安排的结果。”[22]
1.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加速转型,国家对私人消费领域和集体消费领域的解禁,大众化的旅游消费获得了“合法性”基础。众所周知,如同前苏联、东欧等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在改革前的全能主义时期,中国的“社会”实际上被国家“殖民化”了,并不存在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一方面,国家推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政策、“统购统销”政策和“大锅饭”政策,抑制了社会大众的消费能力;另一方面,“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是这个时代反映在消费领域的基本意识形态,旅游消费自然被视为“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遭到抑制[23]。改革以来,随着国家推动的社会结构的变革,带来了社会个体的消费欲望的解放和消费欲望的“合法性”获得。对此,王宁用“国家让渡论”解释了消费主义在中国消费生活中获得合法性的原因,即“消费主义在中国的兴起,是伴随社会结构转型而来的国家让渡民生自由的结果,也是国家在意识形态上从‘乌托邦主义’转向‘经济主义’的副产品。”[23]换言之,随着国家对私人消费领域和集体消费领域的解禁,不仅社会个体的消费欲望得到了彻底的解放,而且消费者对消费产品选择的自主性不断增强。
王宁进一步指出,中国社会的消费制度经历了从禁欲主义向消费主义的变迁。“消费主义的本质,就在于不断追求新的产品和体验,而且这种追求永无满足之日,因为一件产品或经历被体验过了,人们就会逐渐产生厌倦,就会去追求新的产品和经历。正是由于这种求新求变的心理,驱动着人们消费欲望的不断升级换代。”[8]375而旅游向来以求新求奇为特征,通过每一次对不同旅游“吸引物”的消费,产生更强烈地去下一个旅游“吸引物”消费的欲望[24]。这种欲望又促使旅游者永元止境地追求着下一个目标。因此,旅游被视为最能体现消费主义本质的一种消费活动。
2.国家宏观消费制度和旅游管理制度的变迁刺激了旅游消费的发展。房爱卿等学者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消费政策的变迁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即抑制消费政策阶段(1949-1978)、补偿消费政策阶段(1979-1988)、适度消费政策阶段(1989-1997)和鼓励消费政策阶段(1998年以后)[25]。不论这几个阶段的划分是否合理,但从建国之初的国家抑制消费到现在的鼓励消费的转变却是不争的事实。例如: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刺激消费的相关政策:短短几年内连续八次降低银行存款利率,降低住房、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消费税率,征收存款利息税,提高城镇低收入者和公职人员的工资,推行消费信贷,延长节假日(由此形成五一、十一、春节三个旅游“黄金周”)等[22]。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国家对旅游消费的开放和鼓励,各种各样的旅游市场和中介机构迅速发展起来。同时,为了保障消费者的旅游安全,让消费者能够放心旅游,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旅游市场和旅游中介机构的法规或政策。例如:《旅游安全管理暂行办法》(国家旅游局令第1号,1990)、《旅游投诉暂行规定》(国家旅游局第2号,1991)、《旅行社质量保证金暂行规定实施细则》(国家旅游局令第3号,1995)、《旅行社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国家旅游局令第5号,1996,这部法规于2001年和2009年分别被进行了两次修订)、《旅游规划设计单位资质等级认定管理办法》(国家旅游局令第24号,2005)等①。
从上所见,国家的特定制度安排是中国人逐渐热心于旅游消费的合法性基础之一。
3.国家逐步退出对私人生活方式的干预,并逐渐放松对消费生活的话语控制和制裁。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家改变了过去对贪图享乐进行道德鞭挞的做法,开始鼓励居民进行消费[23]。具体而言,国家已不再对私人消费领域实行严密的监控,生产场所和消费场所逐渐分离,彻底改变了私人领域的消费活动过程和结果。家庭不再像前几十年中那样,一切求诸于政府。一方面,个体消费逐渐变成了个体的自主选择过程,另一方面,个体消费者越来越依赖于宽松的商业交易。如此,家庭领域内新的微小的自由实质性改变了国家和人民之间的政治权力关系[26]。
二、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社会学关于旅游消费的解释不同于经济学的经济决定论。“本真论”和“享乐论”从微观视角解释了旅游者个体的不同体验;“日常实践论”从中观视角解释了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之间的动态互动过程,以及对旅游者的日常生活世界产生的影响;“文化控制论”与“制度激励论”从宏观视角解释了旅游消费的社会分层机制和外部激励因素。
我们不难发现,社会学家对旅游消费的解释虽有分歧,但也有相似的观点;1)大众旅游消费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不容置疑,现代社会为社会个体提供了非必需品消费的结构性条件(如收入的增加、交通技术的进步及相应的产业化、带薪假期制度的形成等)和文化条件(如享乐主义的文化、怀旧和寻根情节、媒体文化的影响等)。2)大众旅游是消费主义的伴生物,消费主义以享乐伦理为“合法性”基础。一方面,当享乐伦理获得“合法性”后,旅游消费就成为一种被广为接受和推崇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消费主义与消费社会的物质极大丰富密切相关。“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10]1只有享乐伦理的合法化与消费社会的丰富物质相结合的前提下,大众旅游才得以迅速发展,并成为一种时尚的消费方式。
以上关于旅游消费的社会学解释,对分析转型中国的旅游消费现象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但笔者认为,以下几个问题还需进一步展开。
1.从旅游者的“寻真”过程来看,尽管前辈学者批评了现代社会的旅游“吸引物”大多是被“舞台化”了的,是为了满足旅游者的好奇而“创造”出来的、不真实的产品。但是,不同的旅游者对“寻真”的追求取决于他对“寻真”目标的设定,即不同的旅游者并非对同一旅游“吸引物”的“真实性”获得同样的体验。例如,在转型中国社会,不同的社会群体(如大学教授、工人和农民等)因为拥有不同的文化资本,可能对“寻真”的设定和体验会千差万别。但具体有哪些方面的不同或相似之处,对此需要深入的经验研究才能回答。
2.从“消费主义”来看,不能仅仅把“消费主义”看作是一个关于消费的意识形态的问题,不同国情之下人们对“消费主义”内涵的理解会有不同。西方国家关于“消费主义”的享乐伦理的“合法性”是建立在经济繁荣和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基础之上的,人们对“消费主义”的观点会有高度的相似性。而中国的社会结构尚处于“金字塔”型,中产阶级毕竟还是少数,这种贫富分化的格局导致不同社会阶层对“消费主义”的内涵界定可能存在较大的分歧,这同样需要深入的讨论和分析。
3.从旅游消费的“制度激励”来看,长期存在的“二元”城乡社会结构,导致农民和市民对消费制度的体会也有巨大差异。较之于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民的经济收入、消费观念、消费方式等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巨大差异导致的社会“区隔”依然存在,这不仅表现在经济收入方面,也反映在文化观念以及生活方式方面。城市的高收入群体对一些惯常的旅游景点早已产生了“审美疲劳”,对他们而言,要么去乡村那些自然风光十分优美却未经过人工雕琢的地方,追寻一种返璞归真的原始“真实”;要么将出国游、甚至太空游作为一个重点内容。相反,乡村社会的大多数农民,一方面,由于收入低下,出游的条件和机会大大减少,很难真正分享国家推行的“消费制度”的益处;另一方面,由于长期生活于传统、封闲的乡村社会,相比市民而言,他们对未经“加工”的自然风光兴致较弱,反而更想去现代气息浓郁的城市看看。如此这般,针对不同社会群体关于旅游消费的解释,更需结合经济、制度和文化观念等综合因素提出新的分析思路。
注释:
①http://www.cnta.gov.cn/.
原文参考文献:
[1]Urry J.The Tourist Gaze:Leisure and Travel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M].London:Sage,1990:2.
[2]MacCannell D.Staged Authenticity:Arrangements of Social Space in Tourist Settings[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3(3):589-603.
[3]Boorstin D.The Image:a Guide to Pseudo-events in America[M].New York:Atheneum,1964:3.
[4]科恩.旅游社会学纵论[M].巫宁,马聪玲,陈立平,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
[5]Wang N.Rethinking Authenticity in Tourism Experience[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99(2):349-370.
[6]王宁.旅游中的互动本真性:好客旅游研究[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6):18-24.
[7]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彭强,黄晓京,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8]王宁.从苦行者社会到消费者社会:中国城市消费制度、劳动激励与主体结构转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9]Ritzer G,Liska A."McDisneyization" and "Post-Tourism" in Touring Cultures[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7:3-7.
[10]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1]Turner V.The Center Out There:the Pilgrim's Goal[J].History of Religions.1973(3):191-230.
[12]Cohen E Towards an Agenda for Tourism Research in Southeast Asia[R].Hong Kong:Asia Pacific Tourism Association Fifth Annual Conference Proceedings,1999(23-25,August):10. [13]王宁.旅游、现代性与“好恶交织”——旅游社会学的理论探索[J].社会学研究,1999(6):93-102.[14]吉登斯.社会的构成[M].李康,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428.
[15]乔治·里茨尔.社会麦当劳化[M].顾建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16]张敦福.消费的社会形式及其社会后果——旅游的案例[G]//苏国勋.社会理论:第四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234-246.
[17]尼古拉·埃尔潘.消费社会学[M].孙沛东,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18]Ritzer G.The Globalization of Nothing[M].Pine Forge Press,2004:7.
[19]尚·布希亚.物体系[M].林志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223.
[20]Graham Dann.Anomie,Ego-enhancement and Tourism[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77(4):184-194.
[21]Stearns P N.Consumerism in World History: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of Desire[M].London:Routledge,2001:Ⅸ.
[22]王宁.消费制度、劳动激励与合法性资源[J].社会学研究,2007(3):74-98.
[23]王宁.“国家让渡论”:有关中国消费主义成因的新命题[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1-7.
[24]麦坎内尔.旅游者:休闲阶层新论[M].张晓萍,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86-100. [25]房爱卿,范建平,朱小良.我国消费需求发展趋势和消费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1-13.
[26]戴慧思.中国都市消费革命[M].黄菡,朱强,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4-15.
- 本文标签:
| |
|
| 【分享】 【打印】 【收藏】 【关闭】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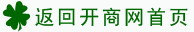 |
- 相关内容
- 更多
- 李怀:旅游消费的社会学解释:传统与前沿 [2017-5-24 10:42:47]
- 李怀生:略论国有企业改制思想工作中的难点 [2010-1-17 11:51:47]
- 李怀简介 [2006-3-31 14:17:31]
- 图片资讯
- 更多














